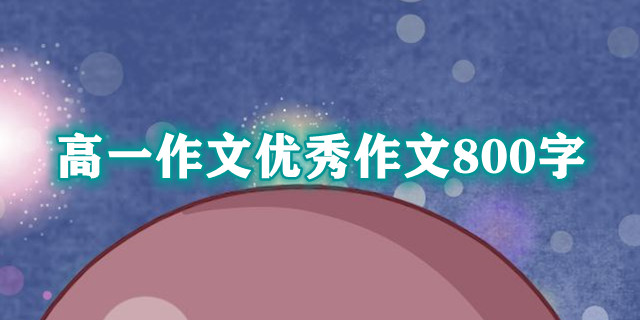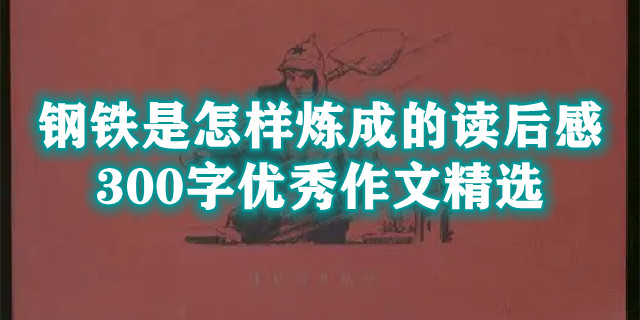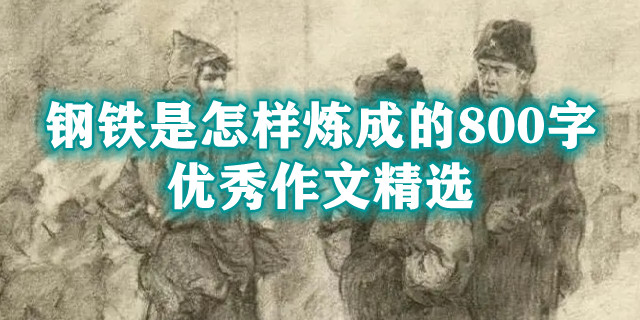黄浦江之魂 800字高考作文
黄浦江尚且“纳百川”,何况文化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河?
立于黄浦江之畔,映入眼帘的是黄浦江与多条河流融汇之景:她向一切到来者敞开怀抱,不因流量的差异而拒斥任何一条支流汇入。她平等、善意地对待、抚慰一切生灵,用轻扬而有力的臂膀推动来往船只徐徐驶去。步履轻盈的激流,在与旁支的对撞中回旋,生出层层涡旋,倏 地又向前激荡开去,飞扬起无数浪花。当她将旁支都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后,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只见前方的河道愈发宽阔,于是原始的力量得以扩充壮大,继而焕发更强的生命活力,步入阔远宏大的生命 境界。
惊叹于眼前景象,我不由得联想到这一方的中华大地:中华文化不正是一条动态前行、水不干涸的浩荡之河吗?黄浦江尚且“纳百川”,何况文化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河?中华文化的发展、文脉的延绵,不正应基于黄浦江这样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的对外态度吗?
尊重是相互的,唯有理性地认可他国文化独有的价值,中华民族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同时,开放包容地允许外来文化在华夏大地上正向地输出,更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的表现。
然而,当下不少人因外来商品在小范围内稍呈流行之势便冠以“倾销”的标签,或因许多年轻人为日漫吸引、为美剧着迷便高举文化入侵的旗帜怒斥其“叛国者”“卖国贼”,盲目加以抵制。这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标榜爱国的背后,是盲目的感性思维逐步消解着理性意识,更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而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结的滋生蔓延,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感降低、国家凝聚力削弱。当然,这绝非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盲目自信便是可取的。清末顽固派固守传统夷夏观念,妄自尊大,无视西方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强大的优势,最终由闭关走向被迫开关,为自己的愚昧无知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两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或是缺乏自信而不愿包容,或是过度自信而不屑开放,都可能导致中华文化之河的长波在拒斥一切旁支的汇入后渐趋干涸,使中华文脉或是因缺乏包容性而走向狭隘,或是因发展受限而走向停滞,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也将随之一落千丈。
自然,这并非意味着“送去主义”崇洋媚外的思潮为佳,更不是说“送来主义”外来文化强势侵略威胁自身文化的现象不值得警惕,只是身为传承了五千年文化的华夏儿女,我们应该有自信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住脚跟,提高包容度,以开放的姿态与外来文化平等、和谐地互动。正如眼前的黄浦江一样,乐于去接触、接纳,拥抱每一次邂逅与融汇。从被动的视角看,黄浦江的精魂启示了我们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输入。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上升,我们还应警惕在发达国家有盛行之势的“文化歧视”在华夏大地上重演-对弱势国家的傲慢与偏见。相较于清王朝盲目无知的自负,这种源于大国地位、看似“理智”的“俯视”或许更为可怖,因为其易于在野心和欲望的驱使下,步入文化歧视,甚至文化同化的陷阱。庞龙笔下曾经的“漫游者”,亦可能成为如今的“守旧老人”。先于中国迈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诸国,在宣扬自由平等中走向偏见局囿的历史教训,便可引以为鉴。美籍华裔政治家骆家辉小学时因吃了虾米、喝了稀饭而惨遭美国老师殴打。食物本来不分三六九等,可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坚守自我文化“最优”,面对“落后”文明,便将其一切都妖魔化,以凸显自己的高贵与优越,食物自然也就被烙上了神圣或低贱的标记,被尊奉或是鄙夷。
残酷的历史教训让我们看到大国付出的代价是最后陷入封闭与焦虑,正如美国迷茫一代与垮掉一代的困境悲歌。不仅如此,频繁的文化对冲下,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一方往往会表现出蚕食,甚至同化另一方文化的倾向,最终可能导致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乃至荒芜。
然而,文化并无尊卑之分,即使是再小的文化,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同信仰,也必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何来孰优孰劣?文化的特殊性不应成为一个国家文化遭受偏见的理由,亦不应成为优越感的来源。我们没有理由因华夏文化的历史悠久便自觉高人一等,何况自负之情的笼罩之下,我们难免会有所蒙蔽、忽视自身文化的诸多问题。通过打压弱势文化来彰显自我文化的优越性,实为自欺欺人,终将在偏见中走向故步 自封。
与其如此,不如借鉴黄浦江“河海不择细流”故而“就其深”的智慧,以探索的眼光挖掘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去芜取精,将能为己所用的元素融入,转化为自身的力量。正如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便是西方的建筑风格与江南传统民居特色的融合,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海派文化,展现了中西融通的文化新气象,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崭新的活力。从主动的视角看,浦江的精魂指引我们如何秉承以自我发展为纲的宗旨来面对异质文化。
由此可见,为了使中华文化永葆丰盈充实,焕发新生活力,我们对外应不盲目拒斥、不无端贬损和倾轧,对内应巩固文化自信,审视并且自省存在的问题,从而构建一种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态度。更进一步说,便是始终从大写的“我”的视角,应用“拿来主义”中去粗取精的思想内涵,转化外界文化的优势为自身服务。
非“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先有开放意识,拓展视界,方地容纳“异己”的存在,再加以探索、挖掘,进而能深刻地认识到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以及外来文化的精华,有机结合两者,将会使中华大文化之河如黄浦江一样,在与旁支的对撞中吸纳、汲取,迈向更为广阔中 生命境界。

而它制衡岁月
那种看是凝视,不是在附近的咖啡吧给阳光熏得昏昏欲睡那样软服地看,也不是重重复复的不算惊鸿的匆忙一瞥。
而它制衡岁月
我在某一天黄昏突发奇想要去滨江看江水。那种看是凝视,不是在附近的咖啡吧给阳光熏得昏昏欲睡那样软暖地看,也不是重重复复的不算惊鸿的匆忙一瞥。从家里骑单车过去不需要太长时间,路上我总共碰到三个人和一部车,他们出现在不同时段,隔得很远,然后一拐,便看不见了。这在上海是很少见的事,它带给我意料以外的镇静与心安。
沿途有秃得差不多的银杏树,扇形的叶片总是安静地成为融化在焦点之外的散景。然而你很难忽略在路上打盹的猫。它们经常挠抓白色的下巴,显得若无其事,怀着谜语倒卧在路上,直到人靠得很近才轻快地跳往平原或树的方向。
如果你未曾到过上海或是没受过伤的黄浦江,我想你会问我关于江河的问题。
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灰。在滨江,偶尔会看到足够年长的形形色色的老者,屈着上身,伏在栏杆上,眼睛经常看着江水的方向。他们的眼睛通常很深,目光泅泳在水间寻找摆动白浪远去的船。江是生命的供给者与索求者。那是灵魂离弃躯壳后会自然飘往的归属之地。因此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灰。那颜色融入太多灵魂,我不具备灵魂的语言,没有能力指认。我只能在这声音、光影的流动里闭上眼。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也站到铁质浮标上-最好是浪来的时候,隐隐约约会感受碎浪飘来水雾的位置,顺着我手指的朝向。彼时你会尝到很淡很淡的咸味,头发与衣服在风中摆动,眼睛凝视天空。关乎这里的一切,你几乎不用说什么就能够明白的。
此时骤雨将至。潮水涨起来了。潮水退下去了。我快步跳下浮标躲到一间展馆。这雨要下好久,门口一个女人抬头说。我一直退到最里的一个隔断的独立地带,这地方有个壁炉样的拱状凹槽,侧边的藤筐里码着颜色温暖的枯柴松枝。我一连丢了三五捆进去,火被压得明明暗暗,然后一下子充塞了炉膛的空间。火光照亮了整间房间,延伸到拱门门口,那边似乎更加明亮,白炽光从前厅照射进来,从我的视角望去,像是处于白昼和黑夜的分界。
柴火明明灭灭,烧得我起了一点儿薄汗。我瞥了眼屏幕,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日军从海上航行而来,闹声枪响在楼宇和连栋的公寓间势如破竹。然后是制衡。十七分钟前的思想在高层云翳的天际破云直上,清角低回,理想与生存,只剩下生存。建筑的玻璃都碎了,墙面参差化粉,几乎没什么可落脚的地方。我不晓得那是谁。我都辨别不清他属于哪国。某个人半跪在阁楼矮柜的棱角处,推翻生命的本能,忘记生命的单薄,持有过去植根的或曾疑心过的信仰的事物。上膛。星星一样滚烫。射击。
后面的几分钟,人们收拾战争的残局。人总要生活,即便命运的本质是屈服于时代的脆弱。没有响动停息下来。人支起货架,人写文章,人收敛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回家,或者收敛自己的心绪回到持枪的地方。我几乎判定不了的震悚。可那是必然的。人们在不断的打散中重新来过。有人选择沉入江底,有人看着江水奔流而哭泣。有人忘记上海有江。人们重新来过。仰望没有火光的天空。这不必有任何多余的矫饰。他们在等。时间跳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门口的女人进来熄掉了壁炉,然后告诉我雨差不多停了,因为骤雨不终日。骤雨不终日。我重复。这是个好词。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念它,真好。像任何一个形似生命、爱和永恒一样的红颜色的、却是与温柔的事物叠加的希求。然而整个房间都是黑的。远处的白炽灯光是盛夏时节的枪火。这是教人狼狈的季节。横陈的亡者没有多长时间就腐化,这几乎是不能否定却确乎难以言说的现实。黄浦江和吴淞江漂着血液。它或曾是从某个年轻人胸膛的穿孔中流出。他们被战争矮化,但或许,我说或许,他们中的某个或曾向往文学和艺术,向往一些绝不只是子弹破空穿身而过的单薄。永恒、山、海、天空。
这样的东西。然而江河漂荡溶蚀的血液。这种灰色,又怎么可能仅仅是灰色本身呢?
十分钟以后,雨暂时收了收。门口的女人说还会再下,叫我趁着这个时隙快点回去。
我朝外走的时候,是铺天盖地的潮和膻。天色沉郁灰重。那真是一场太大的雨,银杏树的枯叶细枝打了蔫,一条一道垂落在街口或者泥土里。一地狼藉。这是自然的代谢。
我并没有那样遗憾。是的,或许你要质询一些事情,关于隐喻,关于纵横时代的节律,关于战争和生命。关于江河汇流的除却水流所有的东西。可是,你知道,玉带凤蝶会在下一个季节陆续羽化,年轻的银杏取代衰亡的银杏,甲虫啃蚀枯枝落叶,菌蕈在雨后四处生长。你知道,变化是常态,死亡也是,就像相遇注定要成为悲伤一样。转圜是必要的,挽回也是,所谓的时代与时代的信仰,也是这样。但这样看不到真的黄浦江,没有谁不垂钓沉入水中的藻,没有谁敢否定生命的薄弱,就像没有谁能够触及永恒的封顶,却都在路上一直走着。
于是我骑着单车,绕着转着。呼吸似的打板,忧伤的小调。潮水涨起来了。潮水退下去了。我的声音埋没在风里,向着世界上任何一条被遗忘的枯竭的河飘去。我要写一封信寄回我所在的某个地方,告诉他们我正在路上,请不要捎来任何那里的新闻、质疑、忧虑,或者要求回复的挂号信。我只是偶然栖息于此的人,没办法把自己的全部扛在身上。不要-不要问我被大雨冲刷得怎么样。不要问风的名字、水流的颜色,或是黄浦江畔的月光是何价值。我知道我绝不会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知道,如果有天关乎这里的一切消亡,我将用余生来为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