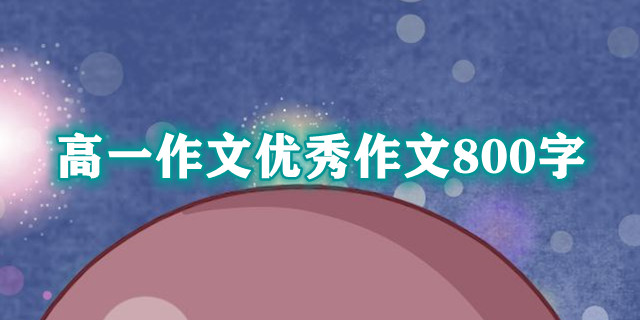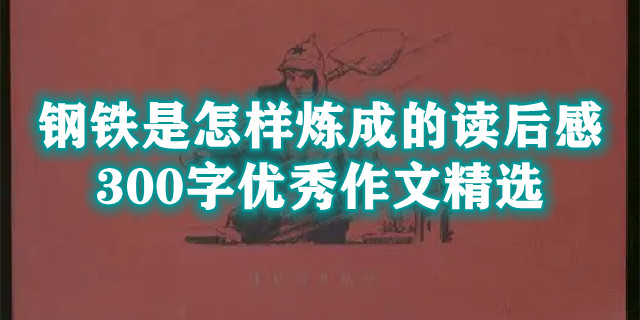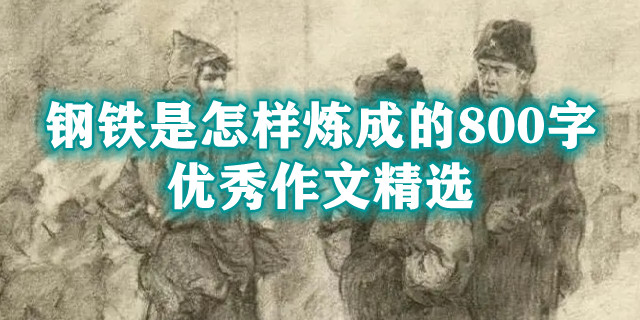放 生 800字高考作文
月光,和楼顶的霓虹灯一起,散落在波光粼粼的黄浦江面上,像印象派的画作。
八月盛夏,黄浦江畔。
20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是法国人开的咖啡馆。弃置了几十年后,店面被拆分成几家弄潮儿的小店,大二的陈就在其中一家奶茶店打工。被围堵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偶尔透过茶色玻璃,望见对面高耸的陆家 嘴“厨房三件套”。
蓝色调的夏天,陈经常下了班跑到杨的家里看鱼。杨的家里养了缸名贵的金鱼,陈最喜欢看水泡眼金鱼,学着那呆鱼的模样把腮帮子鼓起来-
老杨住在小陈楼上,是位十足的上海老克勒。一年四季格纹西装从不离身,裤缝熨得笔挺,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老杨永远只喝自己煮的咖啡。唱片机是少不了的。杨会拉小提琴,他固执地叫这乐器“凡哑林”,就像张爱玲的小说里翻译的那样。
老杨拉完一首柴可夫斯基,拉开窗帘。
老杨家看得到黄浦江,陈站起来和他一起欣赏火红的太阳掉进江里。
“唉,变得真快呀······记得我小时候······”
他颤抖地咏叹着,半是忧伤,半是喜悦。
老杨还在上学的时候,这里曾是他的“根据地”。放了学的学生便三五成群地在黄浦江畔兜兜转转,零零星星搭起的铁棚往往有少年在捉迷藏。船只靠岸时拉响了震耳欲聋的鸣鸣声,混杂了渔民的吼叫,只有少年会觉得趣味横生。时常有小贩挑着竹担走街串巷地吆喝。老杨出身大户人家,零花钱很多,不像他的伙伴们,只能在蜜饯和小人书里艰难抉择。如果母亲和姐妹们喝下午茶,他还能屁颠屁颠跟着去咖啡店蹭半块奶油蛋糕。
对了,是母亲让他学小提琴的······
他不情愿练时,她就骗他:“乖,拉给黄浦江底下的鱼听。”
后来可能有十年吧,这里不再美了。暴乱的人群,硝烟四起,刺目的横幅勒紧了扣着白高帽的人群,喧嚣、斗争······只是一场雷阵雨的时间,老杨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了。
孩提时代的他被人流挤在粗糙的石壁上,小鹿般的目光空洞地瞅着黑黢黢的黄浦江。
黄浦江里会有鲨鱼吗?长着新的獠牙的鲨鱼,吞掉了小鱼的勇气。日历一页页从红色撕成绿色。
老杨最小的女儿在中秋节出嫁了,就像嫦娥奔月后再没回过乡间。午后,老杨西装笔挺地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被铺满灰尘的唱片机围在中间。
他咳了一声。
“老杨!”
恍惚间,仿佛有人在另一个世界喊他。
老杨走到阳台上俯瞰,看到陈跨坐在电瓶车上向他用力挥手。
带你去个地方!他说。
越过黄浦江两岸繁华的地段,车子一路驶向空旷的郊野、麦田、芦苇荡······
寂静无人。陈摘下头盔,江边湿冷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高三前的暑假,我常出来骑行,恰巧找到这里。”
陈找了个桥墩坐下,指着对面的江说:“时被催着长大,心里很慌。但那天回去我很开心。”
“怎么?学文人借风景排遣苦闷了?”
“才不是,只有你这种老克勒才会那么矫情。”
老杨瞪了回去:“别胡说,我哪里老。”
“对,你不老。你只是怕变年轻。”
顽固的老杨别过头去。
良久,陈傻笑着,开口:“我看到了鱼。”
“就在岸边。有一瞬间,有一条鱼-咻一下-蹿了出来。”
杨哑然
他们在桥墩上坐了很久,一直等着,有一条很小很小的鱼,从茫茫的江面跃起。
夏天逐渐过去了。
陈给杨买了件运动卫衣,教会了他怎么用手机买奶茶。国庆节时,陈从大学回来,老杨约了陈去黄浦江边散步。年轻的恋人们手挽着手从梧桐树下走过,笑意盈盈的少年骑着共享单车掠过,夜跑的人群顺着浦江岸线呼哧呼哧地奔来,这其中竟也有些和他年纪一般的老者。
不知为何,老杨只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就像把一副陈旧的金镣铐,从脚踝上摘了下来。
忽然从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快的吉他声······是街头艺人年轻的、毫无章法的歌声。
姑娘长发披肩,青山磊落,气宇轩昂。
她在唱着一
“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
每天上海人看到的黄浦江,都不是昨天那条了。
不是每一条江都能流入海,不流动的江便成了死水。
鱼也跟着江向东旅行,大多时候江水让我们看不见。或许跃出水面只是一瞬间,如果有一个人看到,那就够了。
新的笑声闪闪烁烁地藏在黄浦江畔。
此时暮色西沉,华灯初上。LED大屏幕又滚动起不同的电子文字,很快这里的夜晚将被彻底点亮。
老杨举着两杯奶茶,身体沐浴在城市最后一缕夕阳下,向小陈走来-
雨果说,人们把黄昏的夕阳当作震旦的旭日。小陈觉得恰恰相反。哦,这不是黄昏的夕阳,而是震旦的旭日。
迎着宜人的晚风,他们身旁逐渐聚集起了拍照的人群。
月光,和楼顶的霓虹灯一起,散落在波光粼粼的黄浦江面上,像印象派的画作。
因为有灯,黄浦江再也不会有黑黢黢的时刻了。
老杨鼓起腮帮子,用力吸了口奶茶,甜甜的,比他小时候吃过的蜜饯还甜。突然,他觉得黑黢黢的江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跃,耳畔激起的水花声,如同春雷炸破了雨夜的轮廓:
“听,有鱼。”
黎明时分。
老杨起了个大早,难得没穿西装,套了件小陈给他买的卫衣,提着一个塑料袋出了门。
他站在岸边,蹲下身子,解开塑料袋-
金鱼摇摆着轻盈的红色尾巴,游回了黄浦江里。
老杨注视着红日从对岸的高楼丛林里升起,想起莫奈的《日出· 印象》。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回去,说着:“蛮好。蛮好。”

争渡,争渡
那段日子极短又过得极慢,车、马、相见都很难,但华夏人心与心的距离,却轻而易举地拉近了。
从此凛冬将散,皓月长明。枪响过后,这人间湖畔依旧星河灿烂,那些“孤光一点萤”的晦暗过往,终会随着年轮一圈圈淡去。
己亥末,庚子初,一场突降的灾难裹挟着刺骨的寒风悄无声息地暴发了。确诊人数心惊胆战地跳动着,全城封锁,华夏人紧紧相拥。无数英雄无畏逆行,利剑出鞘,势不可挡。
在申城郊外的我,每天看着这确诊病例一日日像野藤蔓嚣张跋扈地缠缠绕绕地攀,只觉得这疫情离我好远好远。而我又极痴迷史铁生的文章,“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等待了四百多年”。所以我总觉得,人生是像整整齐齐的棋6局,每一个子儿的每一步都有它的安排,像是平行的交通十字。这使得我对这场灾难显得有些不以为意。
上帝召他回去必定有他的道理。十几年来我一直这么认为,这场疫情却生生地剔去了我的想法。疫情暂缓后学校开学的第一堂心理课,像是滚烫的巨石轰地从火山中迸出来极重地砸在了我心上,“乱石穿空,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是在申城远郊的学校,我们老师也是平凡的申城人,却让我感受到我离这场灾难极近极近,那种震撼让我的心灵久久难以平息。
心理老师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就报名参与了对武汉等重灾地区人民的心理咨询和疏导工作。她说到向她咨询过的一位武汉当地青年男子,想来他也是熬了很久终于撑不住了想找个人倾诉,就打通了市政府给重灾地区安排的心理咨询志愿组的电话,随机切入,恰好是老师接的。他对老师说,自己有轻微的精神疾病,疫情当下,惶恐和不安以及久久压抑难以释放的情绪让他的精神一点一点地崩溃了,手头仅有的精神药物已经所剩无几,因为疫情原因甚至连药店都关门了,他痛苦到常常举起凳子砸自己的头,拿脑袋重重地磕向墙壁、桌角,希冀能缓解压抑到快要炸裂的痛苦。他不敢同家人说,只好偷偷拨通了市政府的心理咨询专线。
老师不敢耽搁一点时间,她赶紧告诉青年可以向政府拨打电话寻求药物资源,让采购食材的社区志愿者把药带到他家,老师甚至问了青年的地址,给他所在的社区打电话寻求帮助,让他千万要撑住,人必须要活着,希望才会有所附丽。好几天过去后,青年一直没有再打电话过来,老师悬着的心丝毫没有放下。
直到疫情形势缓和下来,确诊病例曲线呈现的趋势逐步下滑,老师每天接手数十人的咨询,几个月来至少接手了上百人,逐渐要淡忘那位青年时,遥远的武汉那头传来消息,那位青年最终没有熬过去,长眠在温暖的初春。“真正的离别没有桃花潭水,没有长亭古道,只不过在同样洒满阳光的早上,有的人留在了昨天。”
老师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她把脸埋在胳膊里死死地压抑住哭声,她在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有留住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她在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那天多安慰他几句,兴许能让这个失魂落魄的青年回心转意,但是一切都太晚太晚了。那个青年是不幸的,他没有像史铁生那样拥有一个为失魂落魄的人将一切都准备好的安静的地坛,他也没有像史铁生那样在亘古不变的时光和满园的沉寂中悟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那个青年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像史铁生那样在格外狂妄的年纪忽地失了双腿,也没有像史铁生那样在即将碰撞出一条路时失去了那个把满腔爱意埋在心底的母亲,上帝召他回去,让他免受这难熬的苦难。所以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我的老师在疫情最要紧的时刻,每天在电话前奋战到凌晨,甚至最长有20个小时没有休息,连深夜都在为了前来咨询的人辗转难眠。她说到青年去世时,眸子望着窗外,没有看我们任何一个人,眸子里面倒映出窗外阴沉沉的云,有零星几只孤单的鸟儿在长空盘旋。她好长时间没有眨眼,似乎生怕一个眨眼,眼泪就要夺眶而出。
同学们都悄悄挺直了背脊,脸色凝重,我把脸埋进口罩里,轻轻地哭出了声。
疫情原来离我们这么近,这么近······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95后护士胡佩的手的照片,这双本该娇嫩的纤纤玉手,被消毒水、酒精、洗手液腐蚀到伤痕累累,干裂红肿的一道道血痕像是老兵打仗回来脸上挂的彩;22岁的护士朱秀海瞒着父母去前线当志愿者,她对记者说,“我不能哭,哭花了护目镜我就干不了事情了”,晶莹的泪花在美丽的眸子里打转,像是冬日极美的动人心魄的冰晶石,灼灼发光;病房里五日未曾相见的一对医生夫妇,通过声音和眼神认出了彼此,视线深情汇在一起,最终只来得及说上一句“是你啊”,短暂的点头后就匆匆擦肩而过,这简短的三个字却重若泰山,远胜上一句“我爱你”。这不禁让我想起木心曾说过的“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此时此境,动人心魄。
但,一切都还不算太晚。争渡争渡?怎度怎度?中国堪称做了整个世界的模范,雷厉风行,从设计到建成完工火神山医院仅仅用了十天,隔离和消毒措施以及封城措施都及时有效,每个中国人都在出自己的一份力,不只是有在前线抗击疫情的医生、军人,更有像我的心理老师那样默默无闻的社区志愿者。他们,所有人一颗颗炽热的心相互吸引、碰撞、交融在一起,汇聚成华夏最宝贵的精神文化,汇聚成黄浦江的“魂”,汇聚成中国的“魂”。
我想我不该轻信宿命,也不该妄加评论这些遭受苦难的无辜人,他们不该被上帝召走。所幸中国的行动让事情还没那么糟糕,华夏人在庚子年逆天改命,生生把更多在死亡年轮下的人扯了回来。
我立在黄浦江边上,繁华的楼栋里兴许住着许多曾为防治疫情做出贡献的平凡人。那段日子极短又过得极慢,相见都很难,但华夏人心与心的距离,却轻而易举地拉近了,在这个艰难的寒冬里互相依偎着度过了。
走在黄浦江畔和老街上,我想,若是人不来,老街和江畔是没有这些往事的。华夏若是没有一个个华夏人,那瑰丽的五千年雄伟历史也是不会被铸就的,而在无意中被赋予“魂”的山河也不会如此温柔夺目。